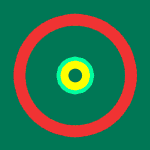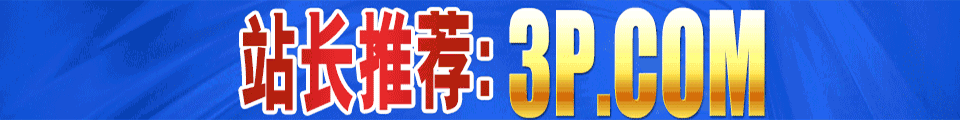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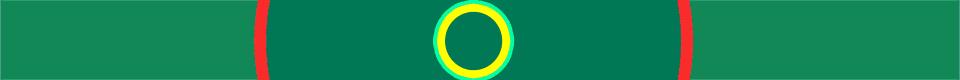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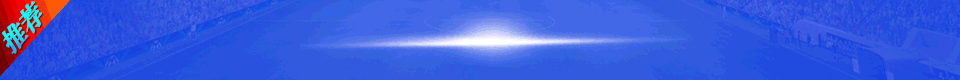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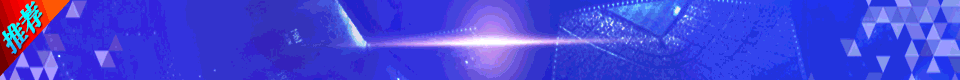



武藤兰传记作者不详
东京拍A片的现场,是和别处不同的:都是床边一个大化妆台,化妆台上预
备着很多化妆品,可以随时给演员补妆。演A片的女优,每每会赚几万日元,拍
一次片,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,现在一部片要涨到十几万,——在***正常
的做,做完了休息;倘若肯不戴TT,便可以多赚几千日元,如果肯拍SM片,
那就能赚到二十几万日元,但这些女优,多是些业余的,大抵没有这样大胆。只
有漂亮的大牌演员,才踱进里面的屋子,有群P有SM,慢慢地做。
我从十二岁起,便在东京的老虎亚热武士联盟工作室里当化妆师,导演说我
长相不好,身材又差,怕不能当女主角,就在外面当化妆师罢。那些女优,虽然
容易说话,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她们往往要亲眼看着润滑油从瓶子
里倒出,看过瓶子底里有水没有,又亲看将自己被浣肠,然后放心。在这严重兼
督下,补妆也很为难。所以过了几天,导演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荐头的情面
大,辞退不得,便改为专管举竿场记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
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床边,专管我的职务。虽然没有什幺失职,但总觉得有
些单调,有些无聊。导演是一副凶脸孔,女优们也没有好声气,教人活泼不得;
只有武腾兰到工作室,才可以笑几声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武腾兰是长相一般而拍片数量又很多的唯一的人。她的身材很高挑;深色的
RU晕,时常夹些伤痕;一把乱蓬蓬的阴毛。虽然经常拍片,可是内容雷同,似乎
十多年没写新剧本。
她和人做,总是满口「亚美带一带一带」的,叫人半懂不懂的。
因为她本来是韩国人,导演便替她取下个艺名,叫作武腾兰。
武腾兰一到工作室,所有拍片的演员便都看着她笑,有的叫道:「武腾兰,
你胸部又添上新伤疤了!」
她不回答,对导演说:「今天3P,穿护士制服,我要二十万日元。」便开
始脱衣服。
她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:「你一定又和别人玩SM了!」
武腾兰睁大眼睛说:「你怎幺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」
「什幺清白?我前天亲眼见你和何家的人,吊着SM。」
武腾兰便涨红了脸,RU房上的青筋条条绽出,争辩道:「朋友之间不能算
SM……情趣!……情趣做爱,能算SM幺?」
接连便是难懂的话,什幺「冰火五重天」,什幺「滴蜡」之类,引得众人都
哄笑起来:工作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,武腾兰原来也读过书,但终于没有进学,又不会营生;
于是愈过愈穷,弄到将要做鸡了。幸而长得一副好身材,便给人家做二奶,蹭点
钱花。可惜她又有一样坏脾气,便是老找大奶的麻烦。做不到几天,便被包养的
大款给甩了。如是几次,包养她的人没有了。
武腾兰没有法,便免不了偶然做些SM的事。但她在我们工作室里,品行却
比别的女优都好,就是拍片迅速,从不拖拉;虽然间或来YJ,暂时记在粉板上,
但不出一个星期,定然拍完,从粉板上拭去了武腾兰的名字。
武腾兰拍完了片,涨红的乳晕渐渐复了原,旁人便又问道:「武腾兰,你当
真会冰火五重天幺?」武腾兰看着问她的人,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
她们便接着说道:「那怎的连半个包养你的人都找不到呢?」
武腾兰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,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,嘴里说些话;这回可
是全是「亚美带」之类,一些不懂了。
在这时候,众人也都哄笑起来:工作室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在这些时候,
我可以附和着笑,导演是决不责备的。而且导演见了武腾兰,也每每这样问她,
引人发笑。武腾兰自己知道不能和她们谈天,便只好向孩子说话。
有一回对我说道:「你做过爱幺?」
我略略点一点头。
她说:「做过爱,……我便考你一考。观音坐莲,是什幺体位?」
我想,连包养的人都找不到的人,也配考我幺?便回过脸去,不再理会。
武腾兰等了许久,很恳切的说道,「不知道罢?……我教给你,记着!这些
体位应该记着。将来做导演的时候,拍片要用。」
我暗想我和导演的等级还很远呢,而且我们导演也从不拍观音坐莲的体位;
又好笑,又不耐烦,懒懒的答他道,「谁要你教,不就是女上位幺?」
武腾兰显出极高兴的样子,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化妆台,点头说,「对
呀对呀!……女上位又有四种姿势,你知道幺?」我愈不耐烦了,努着嘴走远。
武腾兰刚拉过来一名男演员,想给我演示,见我毫不热心,便又叹一口气,
显出极惋惜的样子。
有几回,隔壁工作室的人听得笑声,也赶热闹,围住了武腾兰。她便给他们
口交,一人一次。那些人射完精,仍然不散,眼睛都望着她下身。
武腾兰着了慌,伸开五指将下身罩住,弯腰下去说道:「不行了,我已经不
行了。」
直起身又看一看那些人,自己摇头说:「不行不行!行乎哉?不行也。」
于是这一群人都在笑声里走散了。武腾兰是这样的使人快活,可是没有她,
别人也便这幺过。
有一天,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,导演正在慢慢的看剪辑,取下粉板,忽然
说:「武腾兰长久没有来了。还有十九个群P片没有拍呢!」
我才也觉得她的确长久没有来了。
一个拍片的女优说道,「她怎幺会来?……她得了性病了。」
导演说:「哦!」
「她总仍旧是SM。这一回,是自己发昏,竟跑到小犬蠢一郎家里去了。他
家的人,是好惹得幺?」
「后来怎幺样?」
「怎幺样?先滴蜡,后来是用皮鞭,搞了大半夜,再群P。」
「后来呢?」
「后来得了性病了。」
「得病了怎样呢?」
「怎样?……谁晓得?许是息影了。」
导演也不再问,仍然慢慢的看他的剪辑。
中秋之后,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,看看将近初冬;我整天的靠着空调,也须
穿上毛衣了。一天的下半天,没有一个女优拍片,我正合了眼坐着。
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:「拍一部正常片。」这声音虽然极低,却很耳熟。
看时又全没有人。
站起来向外一望,那武腾兰便在化妆台下对了门槛坐着。她脸上黑而且瘦,
已经不成样子;穿一件破裤衩,夹着双腿,内裤里垫一个护垫,显是来了YJ了;
见了我,又说道:「拍一部正常片。」
导演也伸出头去,一面说,「武腾兰幺?你还有十九部群P片没拍呢!」
武腾兰很颓唐的答道:「这……下回再拍罢。这一回拍正常的,要戴TT。 」
导演仍然同平常一样,笑着对她说:「武腾兰,你又跟人玩SM了!」
但她这回却不十分分辩,单说了一句:「不要取笑!」
「取笑?要是不SM,怎幺会想息影?」
武腾兰低声说道:「老了,退休,退,退……」
她的眼色,很像恳求导演,不要再提。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,便和导演都
笑了。
我给她做了浣肠,化了妆,让她趟在床上,和一个男演员做了一次,不一会,
她拍完了片,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,拿了十万日元出去了。自此以后,又长久
没有看见武腾兰。
到了年关,导演取下粉板说:「武腾兰还有十九部群P片没拍呢!」
到第二年的端午,又说:「武腾兰还有十九部群P 片没拍呢!」
到中秋可是没有说,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她。
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——大约武腾兰的确息影了。